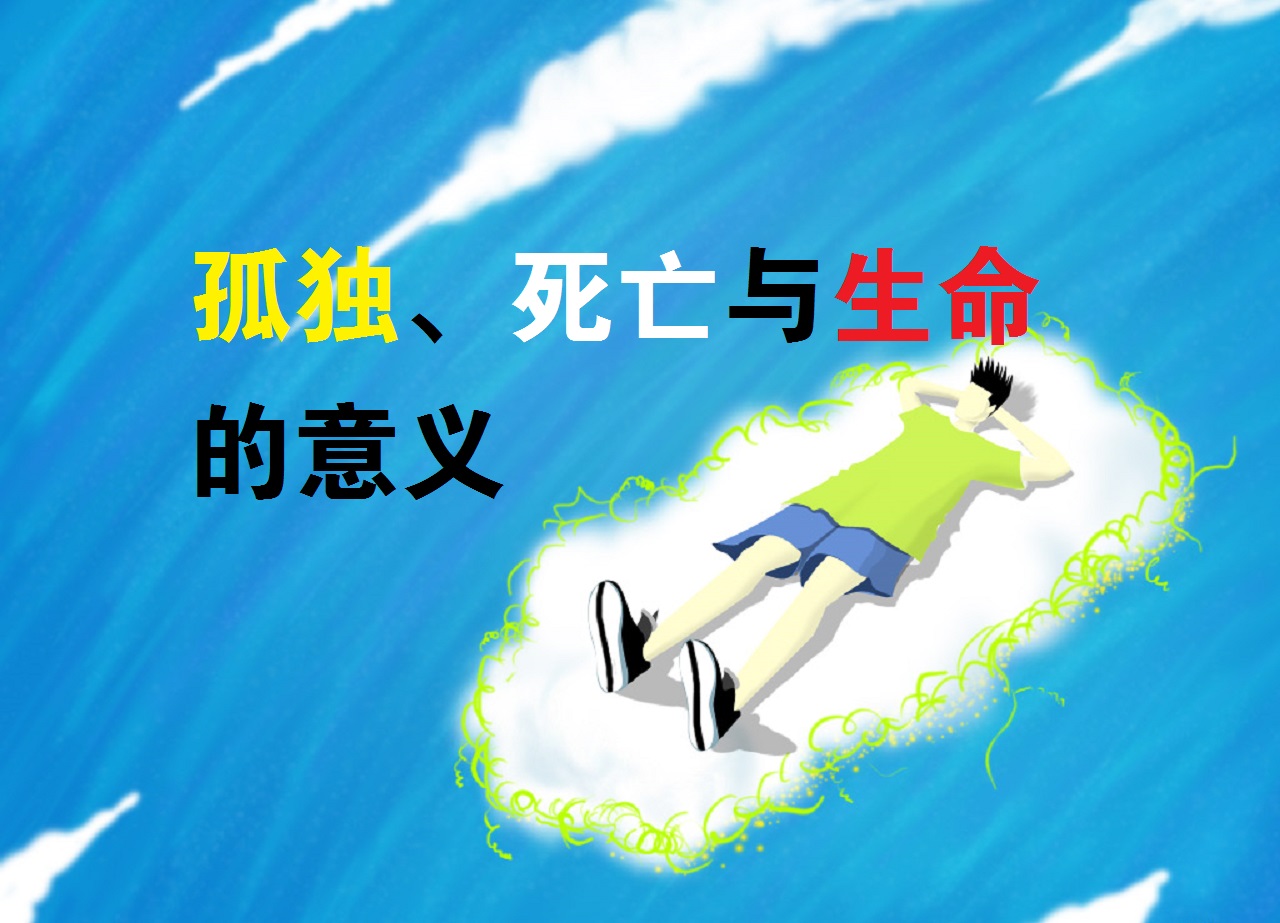人生有两种孤独:一种是日常生活中的孤独;一种是存在的孤独。前者发生在人与人之间,那是一种与他人隔绝的痛苦,这种孤独通常与害怕亲密、担心被拒绝、感觉害羞或是不值得被爱联系在一起,为我们每个人所熟知。
日常生活中的孤独以两种方式发挥作用:一方面,身体健康的人趋向于躲开那些濒死之人,另一方面,濒死之人也被骗进那份孤立之中。他们拥抱沉寂,唯恐把所爱之人拉入他们那个可怕而消沉的世界。一个没有任何身体疾病却陷入死亡焦虑中的人可以体会到同样的感觉。这种孤独毫无疑问伴随着恐惧,正如威廉·詹姆士在一个世纪前所写的: “如果可能的话,没有什么惩罚比让一个人脱离社会,被所有人完全忽略更加残酷了。”
第二种孤独,即存在的孤独则更加深刻,它来自于每个人与他人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这道鸿沟的形成一方面是由于我们每个人都被扔到这个世界上独自存在、独自离开,另一方面来自于我们每个人终其一生都生活在只有自己才完全理解的世界里。
18世纪时康德提出了盛行的常识性假设,即我们都出生并栖居在一个已经完成的、精心建构的、共享的世界中。如今,我们知道,由于神经组织结构的作用,实际上每个人都在构建着自己的心理世界。换句话说,你的头脑中有大量内隐的心理分类系统(比如数量和质量,原因和结果等),当你面临外界的感官信息时,这些分类系统便开始发挥作用,使你能够以独一无二的方式自动地、无意识地构建你自己的世界。因此,存在孤独意味着死亡不仅是指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命丧失,而且包括你个人丰富、神奇、详尽、独一无二的心理世界的丧失,这个世界在其他任何人的头脑中都无法复制。我的回忆——把脸埋进母亲那件波斯羊毛大衣里,闻着陈腐的樟脑味;初中时过情人节,兴奋地瞥着那些女孩子;在一张有着红色皮革桌面、黑檀木桌腿的桌子上和父亲下棋、和叔叔玩纸牌;20岁时和堂弟一起搭了一座烟火台——所有的这些片段,还有其他多如繁星的细节只属于我一个人,而其中的每一段故事、每一个主角都将随着我的死亡永远消失。
我们每个人在人生的各个阶段都以不同的方式体验着人际孤独(即日常生活中的孤独感),而存在孤独在生命的早期比较少见,一个人只有在老了,临近死亡了才会强烈地感受到。在那时候,我们开始意识到自己的世界最终会消失,意识到没有人可以一路陪伴我们走到阴沉的死亡之路的尽头。正如一首古老的圣歌提醒我们的那样:“你只能独自走过那孤独的山谷。”
死亡与睡眠(Thanatos和Hypnos)在希腊文中是一对孪生词。捷克存在主义小说家米兰.昆德拉认为,我们还通过“遗忘”提前体味了死亡。他说:“死亡最可怕的地方不在于让你丢失未来,而在于让你没有了过去。”实际上,遗忘是死亡的一种形式,贯穿于整个人生。
从六岁直至青春期,死亡恐惧还埋在无意识深处,这个阶段是弗洛伊德所谓的性潜伏期。进入青春期,死亡焦虑大规模爆发,青少年会思考这个主题,少数还会有自杀想法,通过冒险行为来对抗死亡。
对于死亡的恐惧有时不会直接出现,它乔装打扮成心理疾病或是一种普遍的不如意感;而有些人却体验到一种明显的、能够意识到的死亡焦虑;还有一些人陷入死亡恐惧,完全不能享受人生的欢乐和满足。
死亡焦虑爆发可引发的两种重要的、安抚心灵的方法:一是留下自己的足迹,获得生命的意义,二是尽可能地活在当下。死亡意识可能成为觉醒体验,它是强有力的催化剂,能引发我们人生的重大改变。
许多人在反思或面临死亡时常常考虑的一个重要主题,也就是说,对死亡的恐惧常常与人生虚度的感觉紧密相关。换句话说,你越不曾真正活过,对死亡的恐惧也就越强烈;你越不能充分体验生活,也就越害怕死亡。尼采用两句简短有力的警句概括了这两层含义,那就是“圆满人生”和“死得其时”——这就像希腊人左巴所主张的那样——“除了那烧毁的城堡,什么都别留给死亡。”萨特也在他的自传中写到:“我平静地走向人生终点……让我把心脏的最后一次跳动印刻在我最后一页作品上,死亡只能带走我的尸体。”“成为你自己。”——尼采规劝我们避免无意义的人生,充实自己,实现自己的潜能,充分的、完全的活着。
这让我想到了“波动影响”,它是指我们每个人,即使没有意识层面的目标或这方面的知识,也都会形成中心影响力,影响周围的人许多年甚至许多代。最基本的“波动影响”是——每个人死后在分子水平上又将重新成为自然的一部分,重新为未来的世界添砖加瓦。最近,一位年轻人因他的婚姻问题来找我咨询,他告诉我,他之所以来找我部分是为了满足他的好奇心。二十年前,他的母亲预约我做了几次咨询,总是向他提到我,并且告诉他治疗如何改变了自己的人生。也许,每个治疗师(和教师)都不会对这种持续多年的波动影响感到陌生吧。
狄兰·托马斯(Dylan Thomas)曾说过,虽然爱人走了,爱却永存。生命的影响互相传递,其中蕴含的智慧、美德和同情心也将代代相传,直到永远。
选自:欧文·亚隆《直视骄阳》来源:心悦荟
图:wallcoo.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