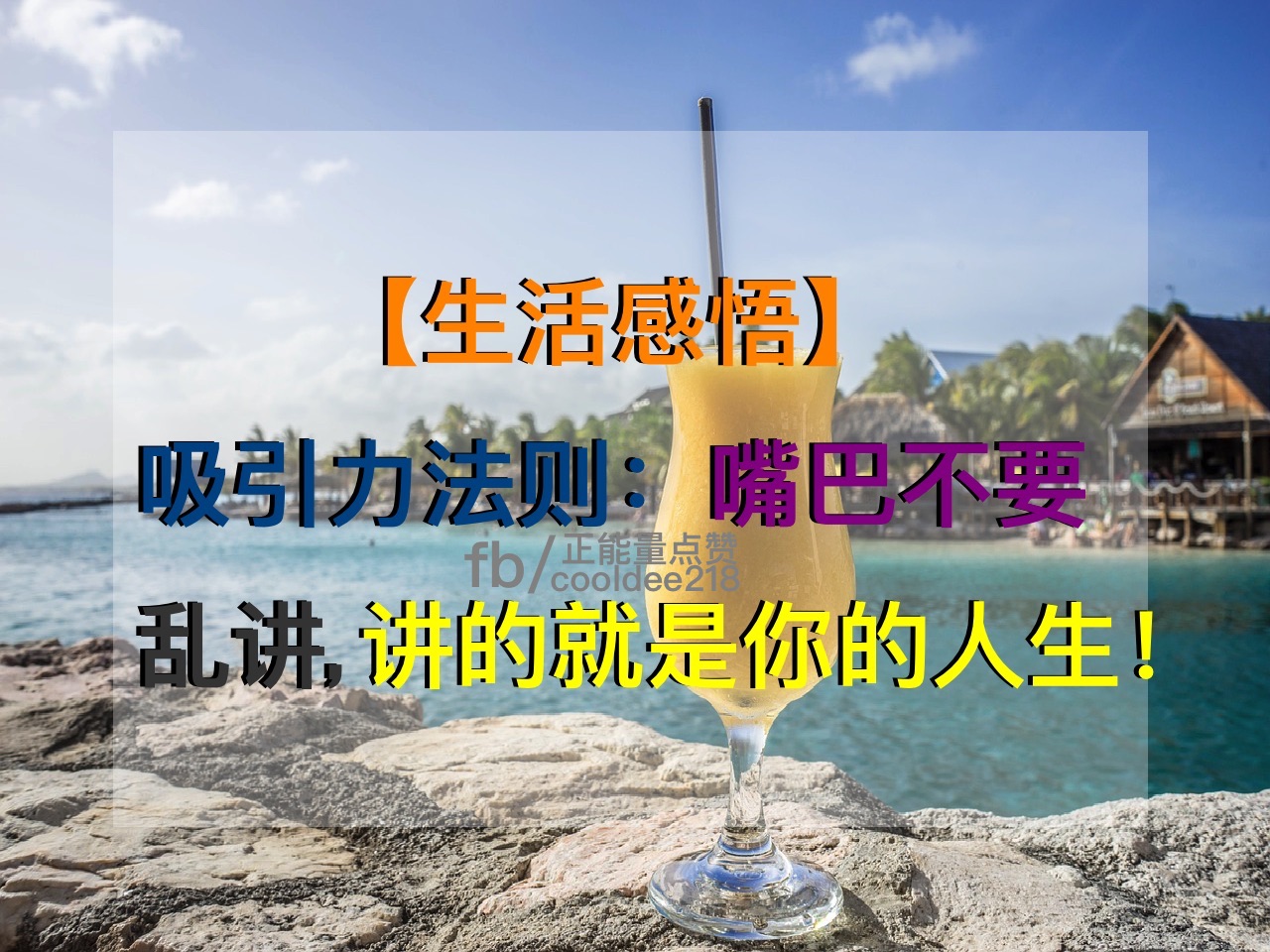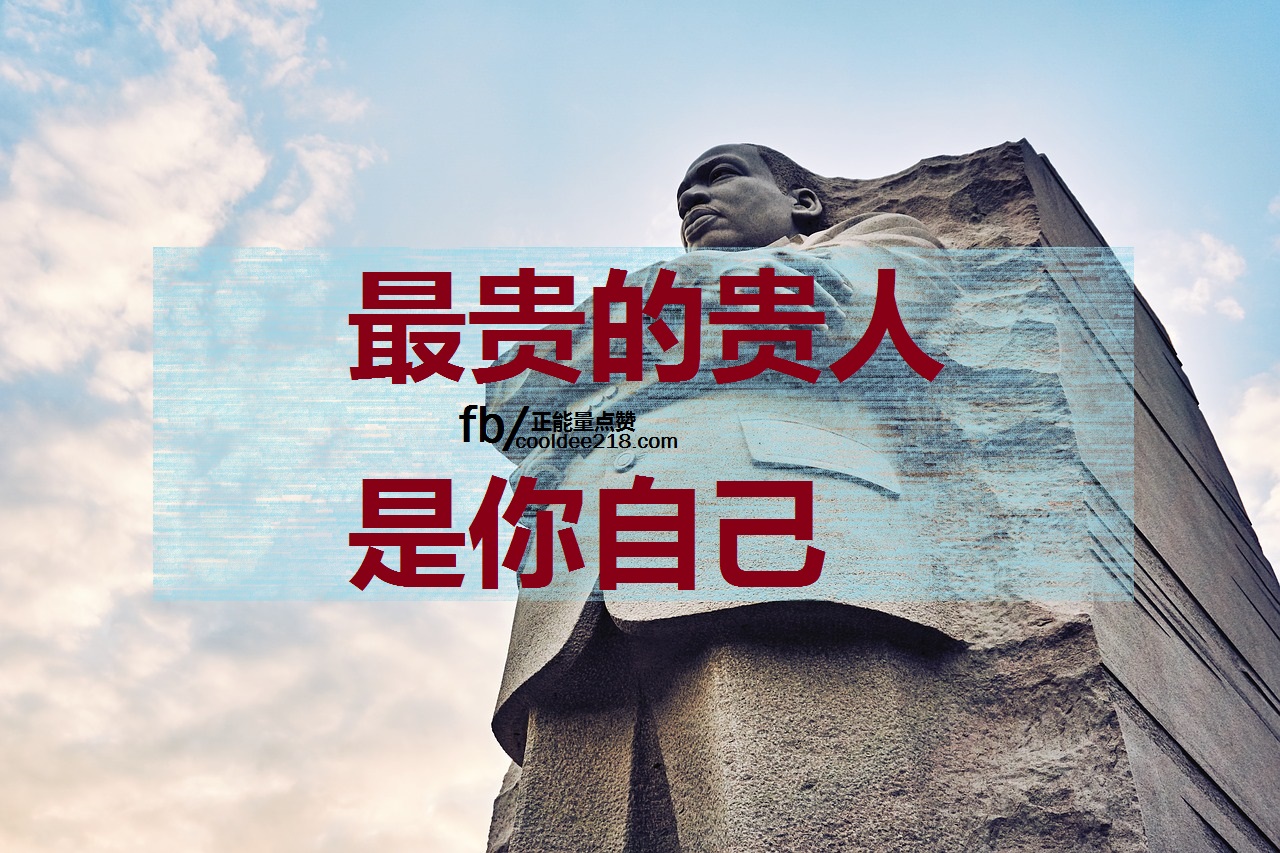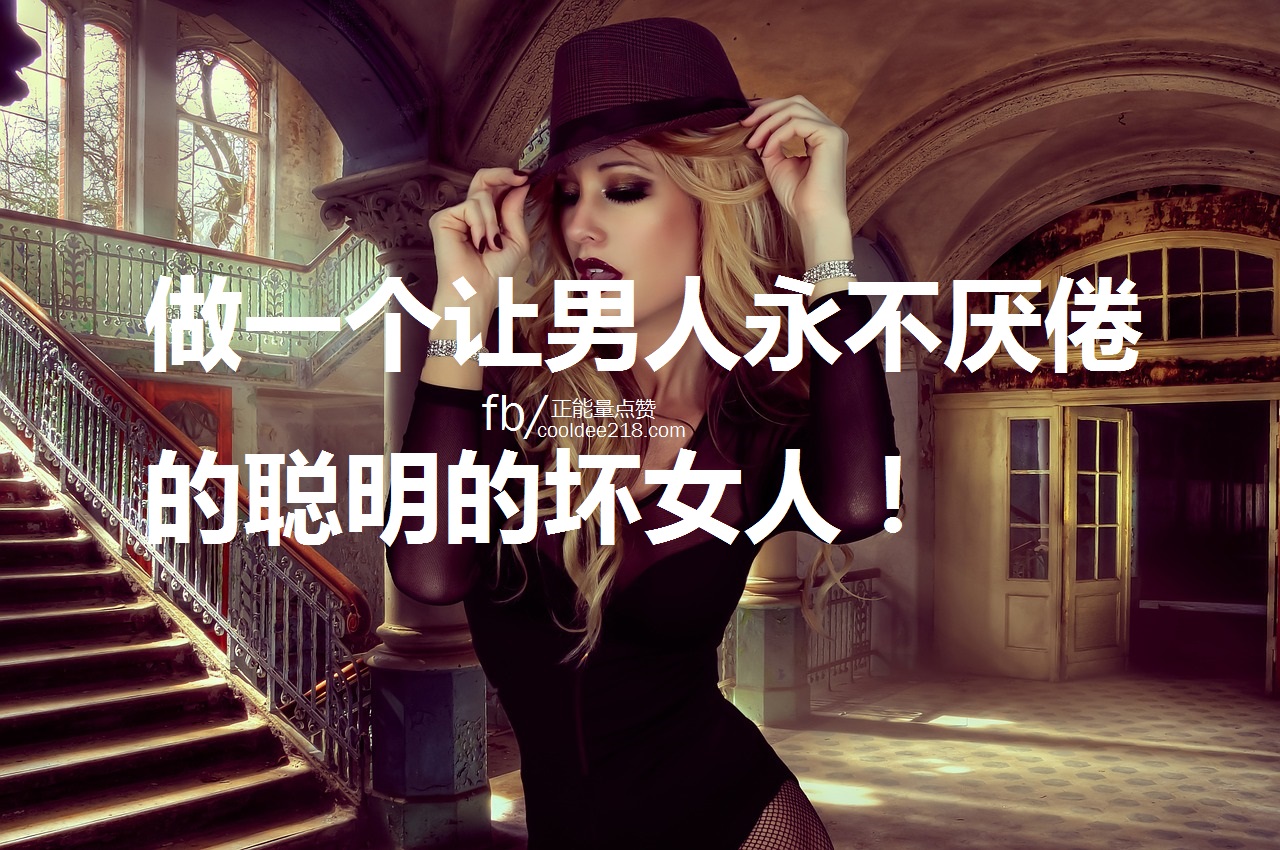在学生时代,我们总是会有一两位形影不离的好朋友,做什麽事情都要在一起,甚至连上厕所都要相约对方,比双胞胎还亲密。一直到现在,还有时候会因为好朋友的忽略或是因为一些小事而闹别扭,就好像是情侣一般的「占有慾」,深怕别人会抢走你的闺蜜。而这些有点「荒唐」的行径,其实你也不用太在意,代表着你与这位闺蜜有着密不可分的感情,把对方当成情人一般呵护对方: 常常在对方面前宽衣解带 朋友之间通常还是会有一定的距离,但一起相约上厕所对你们来说已经是家常便饭,就算要你们在对方面前脱光换衣服或是一起洗澡根本就不是什麽难事,你们一点也会担心对方的身材是不是比自己好,或是自己的缺点被看见,就像跟交往已久的男朋友相处时候一样自然。 对方身体上的细节,你都了若指掌 既然都不在乎在对方面前裸体了,姐妹们的胸型尺寸大小、身上那里有特徵或是有什麽特殊的胎记,你们一定非常了解。有些更亲密的闺蜜,甚至会连对方胸部或臀部的触感都比男朋友还能分辨。 牵手、拥抱、亲吻你们一样也没有少 很多女生的友谊是需要靠肢体碰触来增加彼此间的亲密感,所以走路的时候勾手,常常抱来抱去,对方生日或是友谊纪念日时,你们也不排斥嘴对嘴的亲吻,两个人的感情比亲姊妹还亲密。 对方「有状况」的时候,你比妈妈还担心 只要对方一生病或是心情不好,你恨不得24小时照顾她,陪伴她,不定时关心他是否饿了,想尽办法让「坏掉的」她快点好起来,跟你一起继续冒险,你们没办法自己一个人继续前进。 对於对方的前任,你们都不屑一顾 欺负闺蜜的人,一律列入永不往来的名单之中,尤其是可恶的前任,你恨不得将对方从地表上移除,从此消失在这个时空当中,不再让他有机会伤好姐妹的心。 你们注意对方的小改变 有时候染了头发或是换了不同的造型,要等男朋友的赞美大概需要等到天荒地老,他都还不一定发现,或是随便赞美两句就想要打发你而已。但闺蜜马上一定会发现你今天头发分不同边,脸部妆感哪里不一样,甚至你心情上的一点小变化都能马上发现,给你的赞美或批评都是最真心。 责任编辑:Mia 图来自:google.com
Read more